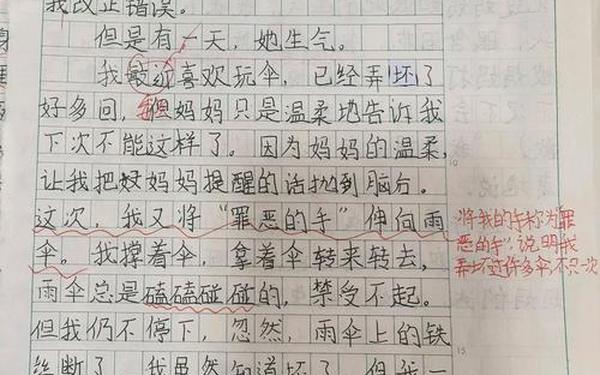最后一节自习课,我总忍不住抬头看前排那个空座位。窗外的银杏叶打着旋儿落在徐小航的课桌上,压住了他昨天没带走的数学卷子,那道没做完的几何题还留着铅笔反复涂改的痕迹。
班主任说徐小航请了病假,可我知道不是这样的。上周五放学时,我看见他把书包狠狠甩在走廊墙上,作业本哗啦了一地。"我受够了!"他冲着电话吼,声音里带着哭腔,"你们除了成绩单还看得见别的吗?"冰凉的瓷砖映着他发抖的肩胛骨,像是被暴雨打湿的蝴蝶翅膀。
今天课间操时,我在器材室发现了他。缩在跳高垫堆成的堡垒里,膝盖上摊着本《飞鸟集》,泛黄的书页间夹着片枯叶书签。"你看这句。"他哑着嗓子指给我看,"鸟翼系上黄金,这鸟便永不能翱翔。"阳光从气窗斜斜切进来,照见他手腕内侧用红笔画的表盘,时针永远停在凌晨两点。
放学路上他给我看手机备忘录,整页整页的日程安排精确到分钟,连上厕所都标注了时限。"他们说考上重点高中就能轻松了,可是..."他踢着石子突然哽咽,"我好像被装进罐头里的沙丁鱼,连呼吸都要按说明书来。

教学楼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。徐小航把书包甩上肩,校服拉链在暮色中闪着微光。"明天帮我请假吧,"他说,"我要去江边看真正的飞鸟。"我望着他走向与补习班相反的方向,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,像道终于松开的弹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