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节的清晨,细雨如丝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艾草的清香。我跟着父母回到乡下老家,踏上那条通往祖坟的青石板路。路旁的柳枝垂着新芽,奶奶说这是"清明插柳"的习俗,寓意驱邪纳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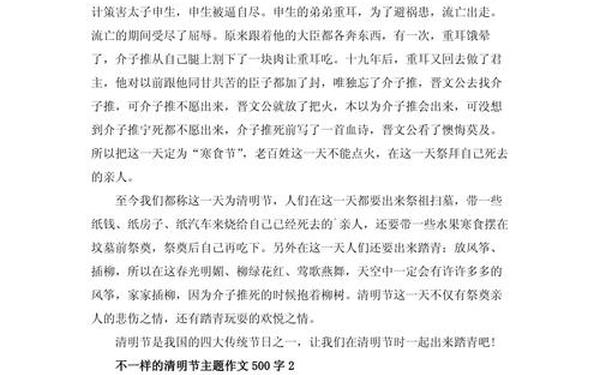
祖坟坐落在半山腰的竹林旁,爷爷用镰刀仔细清理杂草,又在坟头压上几张黄纸。妈妈摆出青团和苹果,轻声念叨:"太爷爷最爱吃甜的。"我学着大人的样子点燃三炷香,青烟袅袅升起时,忽然想起去年太奶奶还在灶台边教我包艾饺。她总说:"青团里的艾草要揉够时辰,祖宗才尝得出心意。"如今案板前只剩那根磨得发亮的擀面杖,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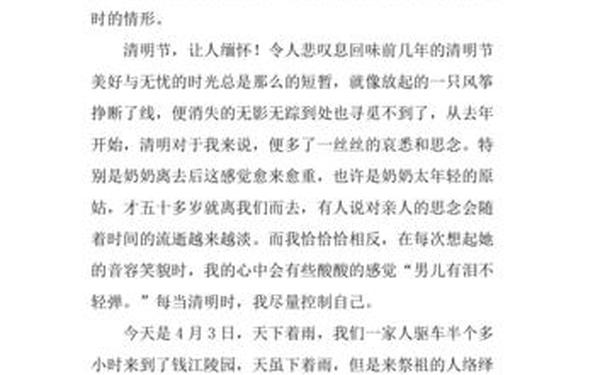
下山时路过烈士陵园,花岗岩纪念碑前摆满了白菊。老师曾说,这里的英雄们牺牲时比爸爸还年轻。我踮脚将亲手折的纸鹤系在松枝上,风起时,千纸鹤与红领巾一同飘扬,恍惚听见历史书里的冲锋号角声。
归途中的油菜花开得正好,父亲指着远处新翻的田地:"清明前后点瓜种豆,农时可不等人。"忽然明白,这节日不仅关乎怀念,更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。就像村口那棵百年老槐,岁岁枯荣间,根脉始终深扎故土。
暮色四合时,雨丝又密密织起。窗台上,太奶奶留下的铜香炉升起缕缕轻烟,仿佛在续写未尽的叮咛。我摊开日记本,将沾着泥土的柳叶夹进纸页——明年的清明,这抹新绿又会催开多少思念与希望?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