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影《活着》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,由张艺谋执导,葛优、巩俐主演,以跨越半个世纪的历史为背景,通过主人公徐福贵的一生,深刻诠释了“活着”的哲学意义。影片用平凡个体的命运折射时代的波澜,既是对生命的礼赞,也是对人性坚韧的致敬。以下从主题、人物、象征三个维度展开观感:
一、生命的坚韧:在绝境中寻找希望
福贵的一生是苦难的叠加:从纨绔子弟沦落为底层农民,经历内战、大跃进、文革等历史洪流,先后失去父母、儿女、妻子,甚至外孙。但每一次打击后,他仍以“活着”为信仰,如老牛般匍匐前行。电影通过福贵与春生深夜对话的经典场景——“咱得好好活着”,展现了人在绝境中迸发的生命力。这种“苦中寻乐”的态度,正如福贵对孙子馒头说的“小鸡变鹅,鹅变羊,羊变牛”的寓言,传递了希望永存的信念。
二、历史与个人的共生关系
影片将福贵的命运嵌入中国近代史的齿轮中:赌输家产反而因祸得福(龙二被枪决),内战中被俘却因皮影戏保命,大跃进时期儿子有庆因过度劳累被墙压死,文革中女儿凤霞因医疗事故丧生。这些情节揭示了个人在时代巨轮下的无力感,但福贵始终以“活着”对抗荒诞。皮影戏作为贯穿全片的意象,从娱乐工具到谋生手段,再到被焚毁的“四旧”,最终成为装小鸡的容器,隐喻着传统文化在动荡中的嬗变与重生。
三、“活着”的双重意义:幸存与超越
电影对原著结局进行了温情化改编:福贵与家珍、女婿、外孙围坐吃饭的场景,比小说中“仅剩老牛相伴”的孤独更强调“延续”的意义。张艺谋用近乎纪实的镜头语言(如巩俐饰演的家珍默默吞咽野菜粥)展现底层人民的生存智慧。福贵不再是余华笔下“为活着本身而活”的麻木者,而是在苦难中提炼出“活着就是一切”的顿悟。这种改编既保留了悲剧内核,又注入了人性光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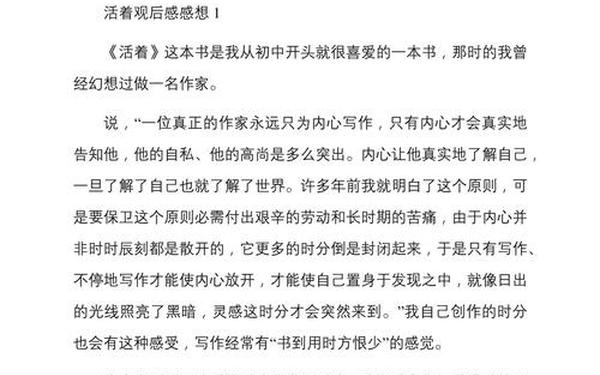
活着的诗意与力量
《活着》的震撼力在于其“举重若轻”的表达。葛优的演技将福贵从浪荡到沧桑的转变刻画得入木三分,巩俐则以沉默的坚韧诠释了传统女性的伟大。影片结尾,夕阳下福贵牵着老牛远去的背影,与开场的喧闹形成强烈对比,完成了对生命的史诗性书写。它告诉我们:活着的意义不在于规避苦难,而在于接纳命运并与之和解。正如余华所言:“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呐喊,而是来自忍受,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。”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