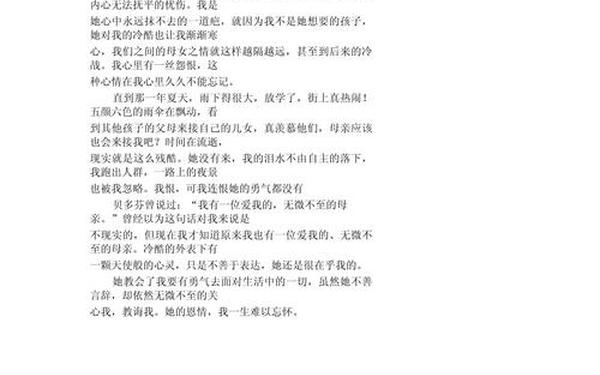运动会当天,我蹲在跑道旁系鞋带时,听见看台上传来细碎的议论。"那个戴红色护腕的女生就是五班的病秧子吧?"我下意识把护腕往袖子里藏了藏,手腕上还留着上周打点滴的淤青。
发令枪响的瞬间,我的双腿突然像灌了铅。明明每天放学后都在操场加练,此刻喉咙却泛起铁锈味,眼前跑道在热浪中扭曲成蜿蜒的河流。拐弯时我重重摔在地上,膝盖火辣辣地疼,掌心被煤渣磨得通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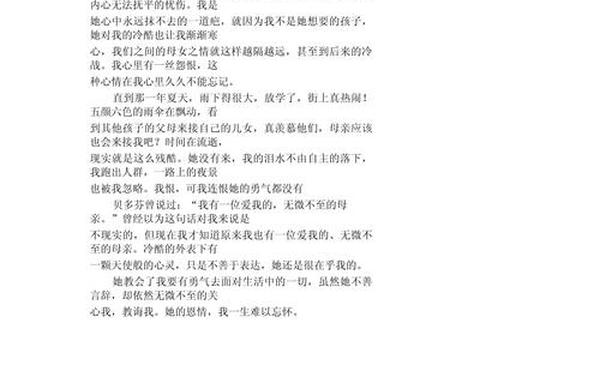
弃权吧!"裁判举着黄旗跑过来。看台上此起彼伏的惊呼声里,我忽然想起上周五的暴雨天。体育老师撑着伞站在操场边,看我在积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圈。当时他说:"丫头,倔强有时候是种天赋。
我撑着膝盖爬起来。血珠顺着小腿往下滑,在白色运动袜上洇出梅花。观众席的私语渐渐变成整齐的加油声,跑道旁医护老师端着碘酒追着我跑。最后一圈时,我的运动鞋里已经浸满汗水与血水,却感觉前所未有的轻盈——原来当一个人真正拼尽全力时,疼痛也会长出翅膀。
冲过终点线时,我是倒数第二。但当我被同学们架着去医务室时,听见广播站正在念我的投稿:"跑道教会我最重要的事,不是如何赢得漂亮,而是怎样优雅地跌倒,再从容地站起。"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是给倔强的灵魂盖上金色邮戳。
现在每次晨跑经过看台,我总会摸摸手腕上的红护腕。它不再是为遮掩,而是像枚永不褪色的勋章,纪念着那个在尘土里开出花来的下午。